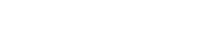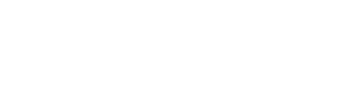對話|數字化育種技術體系的搭建
原發表日期:2022-06-30
來源:中國畜牧業協會
6月16日,由中國畜牧協會主辦,中國畜牧業協會智能畜牧分會、信息分會、豬業分會、禽業分會、羊業分會、中畜傳媒、農信研究院【數字農業大家談】聯合舉辦的“畜牧產業育種智能化線上討論會”召開。
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創新發展處二級調研員厲建萌、中國農業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副院長劉劍鋒,北京農信數智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智慧管理平臺總經理李天平,北京市華都峪口禽業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家禽研究院院長吳桂琴,天津奧群牧業有限公司研究員、技術總監張清鋒,廣東艾佩克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王希斌參會。
與會專家圍繞畜牧產業育種智能化的發展背景及企業應用現狀等方面做了主題報告。隨后,中國農業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副院長劉劍鋒擔任專題討論會主持人,同四位企業代表一起圍繞智能育種做了深入交流,以下是專題討論會文字介紹:

01劉劍鋒對話李天平
劉劍鋒:育種技術跟數字技術結合,實施起來有哪些難點?
李天平:育種和數字化結合方面,以前只能稱為育種信息化。育種的核心關鍵在于數據的采集,過去各個企業或者豬場更多的是依托軟件來實現數據單據式采集,但是不能做到實時和智能化。同時,企業跟企業之間、豬場跟豬場之間,難以實現數據的流通與追溯,導致行業數據未能得到高效的共享。而這與技術架構有關,過去可能還沒有云的概念,大部分以軟件的形態存在,因此在技術實現上是有難度的。
第二,育種工作本身是系統工程。數字化育種需要建立行業統籌平臺來實現數據的流轉和共享。只有依托行業大數據平臺之后,各主體才能基于這個平臺獲得自身想得到的收益。否則,每個主體都有自身的獨立軟件,那其實在整個行業發展過程中,并沒有促進行業更好的發展,每個企業或者個體都是一個“數據孤島”。所以說,過去只能叫育種信息化,還不能叫數字化。信息化只是把紙質單據的數據采集過來,做一個基本的流程管理,但真正的數字化是應該通過智能化采集,結合一些設備,進行大數據流動,形成大數據挖掘。把數據共享出來以后,反哺給所有的企業去應用。但是這個需要一個建設過程,我想這個目前也是在國內技術實現上的一個難點。
第三,結合難點可能在計算能力上。因為單體軟件計算能力有限,如果需要進行大規模的計算,那么它對數據的分布式計算能力要求較高。因此,需要借助當前的互聯網平臺及云計算技術,特別是通過分布式計算來提高計算效率,同時也能提高計算的準確性。
因此,我想可能在這三個方面,是目前育種技術和數字技術結合的難點,同時也是未來數字化育種的發展趨勢。
劉劍鋒:農信互聯在生豬產業數字化及數字育種領域起步較早,談一談農信互聯的工作對推進行業發展起到了哪些作用?
李天平:農信互聯多年來深耕生豬產業鏈數字化改造和產業升級,在推進產業發展方面農信互聯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是產品研發,農信互聯圍繞生豬上下游產業鏈,涵蓋生豬核心場、育肥場等,形成了一體化閉環。根據各產業主體及環節形成了整體數智化提升解決方案。
第二,農信互聯在生豬產業以外,還搭建了一個服務于農業產業的數智化平臺IAP,包括禽產業、羊產業等。基于農業產業數智化IAP平臺,未來畜禽產業育種的數據及算法等技術能得到更好的優化和應用。
第三,農信互聯基于自身在研發人員、分布式計算、人工智能、算法等方面的優勢,可以實現行業整體大數據的挖掘,幫助主體科學決策,實現數字育種技術的改良及數據共享。同時,借助農信互聯的產業數智生態平臺,可以幫助行業所有主體,來實現數據共享和流通機制,促進整體產業的健康發展。從戰略上來講,農信互聯更多的是做產業基礎設施,也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未來在育種行業,把這種基礎設施的平臺建起來,幫助我們把育種產業的“卡脖子”技術進行整體提升。
劉劍鋒:數字化和育種技術的結合實際上是交叉學科,是互聯網技術和常規育種技術進行整合,產生“1+1>2”的效果。也打通了數字育種的最后一公里的困難,給育種企業賦能,起到一個很關鍵的作用。希望農信互聯在育種領域,能給整個行業起到更好的推進作用。
02劉劍鋒對話吳桂琴
劉劍鋒:對于企業而言,能夠在育種一線使用的,有哪些實際技術?又有哪些技術是處于開發或者儲備階段?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在育種成本以及提高效率方面,實際效果如何?
吳桂琴:數字技術與育種技術的結合,在豬、牛、羊等領域,從理論端到實際應用端,中間差距較大。以我們公司育種系統為例,公司最早從08年左右開始設計數字育種系統,整體藍圖設計及基本架構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十幾年來,公司每一年都在不斷地優化落地,用更新的技術去更新。過程發現,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比如說在蛋雞、肉雞領域,數字技術應用比較成熟的,是稱重及產蛋數字記錄這些技術。因為對于蛋雞來說,傳統記錄過程工作量很大,所以這是第一個先解決的。后續的話,結合超市電子稱等理念,數字稱重技術也得以實現。但是目前,很多儀器設備,我們去把它按照物聯網思維進行系統鏈接的過程中,會受到第三方通訊協議制約。比如我們有些設備是進口的,需要我們去跟這些國際儀器設備公司進行溝通,拿到通訊協議允許后,才能夠實現設備跟內部系統的鏈接,推動數字技術在整個應用端的快速應用。所以這些是一些比較成熟的應用案例。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儀器設備,由于專業性很強。在儀器設備鏈接的過程中,因為進口儀器公司的通訊協議不發放給公司,所以我們就做不到。這個也是目前進口儀器設備的現狀,主要受儀器設備方通訊協議的制約。包括像在蛋雞這塊,數字育種技術大部分都相對應用成熟了。
技術儲備方面,比如說在肉雞領域這塊,我們目前一直在研究耗料的自動稱量技術。這個是我們一直沒有突破的。對于肉雞而言,這塊兒技術也是更大的一個挑戰。目前來說,耗料自動稱量主要采取半自動半人工相結合的一個方式。還沒有像蛋雞產蛋、稱重等去實現一個自動化的過程。這些技術在現在包括未來,都是我們需要重點要去突破的。
因為育種產業真正的基礎底層架構來源于表型基礎大數據的積累,只有表型的基礎數據采集精準,數據積累量增多,才能夠實現上層遺傳評估中基因組的選擇能夠更加精準。所以隨著技術的進步以及儀器設備的跟進,整個應用層面也會不斷完善。
數字育種技術,短期來看,對于企業而言可能投入較大。但從長期而言,整體是節約成本的。第一個是人工成本會大幅下降,第二整體效率會提升,第三,數據采集的準確度會有所提高。未來,從遺傳育種理論而言,因為掌握了育種的背后規律,通過數字育種技術,可以實現商品代性狀的判斷。但是目前來看,跟我們預計效果會有所偏差,這主要取決于對表型數據積累的準確性。然后通過上層可實現遺傳育種值的精確評估。因此,對于數字育種而言,底層育種基礎數據的收集是一個不斷升級、不斷更新的過程。
劉劍鋒:剛才桂琴博士給我們分享了兩個觀點,其實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兩個環節。第一個就是數據的產生端和數據的采集端之間要無縫地對接。產生數據之后,如何來傳輸到育種的決策系統來進行使用的,這里面要有一個數據堆積的環節,這個技術要解決。第二個觀點就是產生數據的底層,對數據的質量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只有采集到準確有效、有用的數據,后面的精準育種才能成為可能。
03劉劍鋒對話王希斌
劉劍鋒:如何在企業系統開發過程中,解決育種系統和生產系統可能存在的矛盾問題?
王希斌:在實際育種過程中,確實會存在育種和生產的矛盾問題,比如說,養殖場育種數據采集的顆粒度要求與生產上以群體數據為基礎的顆粒度要求是完全不一樣的。那么怎么看這個問題呢?要想獲得準確的育種數據,我個人覺得這是人員的問題。育種數據采集主要依靠人來進行,而靠人去管理,就是你的“指揮棒”的問題,你的“指揮棒”定的是客觀的,當然采集來的數據是真的。“指揮棒”定的是不客觀,那么數據就變成是假的。
為什么呢?因為現場操作的人員,他們有各自的利益。數據采集如果是由人來進行的話,這就必然會帶來這個問題。舉個例子,比如說繁殖性能中的豬繁殖性能產仔數、活仔數等數據。如果管理人員以活仔數、產仔成功率等不同指標對生產人員進行考核,那么他會為了個人的利益,去做人為的改變或調整。另一方面,要想獲取準確的數據,盡量采用一些現代設備。比如說物聯網設備、性能測定設備以及視頻影像等做一些體型外貌的評估與度量。但是在實際應用過程中,部分設備應用較少。以電子耳牌為例,目前國外進口的電子耳牌性能穩定,但是成本較高,因此應用較少。
所以從數據采集端,無論是通過物聯網設備還是人為進行,最關鍵的是實事求是的問題。那么如何做到實事求是,那是靠“指揮棒”的問題。僅僅通過道德水平來制約管理人員的整體素質,這個整體較難實現。因此,生產和育種存在的矛盾問題實則是企業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問題。比如在非洲豬瘟剛開始爆發的時候,由于大量母豬場種豬被捕殺掉,豬價售價因此非常高。企業則會提前出欄,乃至于核心群的育種工作也很難保證。因此,如果公司利益僅僅來源于原種,那么它受市場波動影響較大。而如果利益來源于商品端,有商品端反哺育種工作,那么這個工作就是可持續的。只能說企業能從中真正得益的話,他們就會堅持。如果,企業經常不得益,那么就會出現引種、退化、再引種的難題。
04劉劍鋒對話張清峰
劉劍鋒:在肉羊數字育種方面,您有哪些體會或者想法?
張清峰:肉羊產業與生豬產業不同,具有品種多、小而散的特點,一方水土養一方羊。近年來,隨著產業規模化程度的提高(特別是3000只以上規模,近年來平均增幅在50%左右),出現了10萬只單體規模的羊場。規模化養殖程度的提高,推動養殖方式和育種思路發生巨大變化。像剛才提到的生產和育種這個關系都是如何去疏通,基于物聯網基礎上的信息化育種工作的開展也好,也是一個主要的問題。之前的育種是生產育種,因為有了這個信息化以后,讓生產育種變成了育種生產。
第二,在企業運營過程中,生產技術人員和育種技術人員是有矛盾的。以我們企業為例,育種部需要定期開展性狀測定工作,而這個過程需要生產部門進行配合,無形中增加了勞動強度和工作量,另外也會影響相關人員的績效。因此,對于育種而言,去收集相關性狀數據常常得不到其他部門的配合。
后來,由于有了信息化和物聯網設備,公司進行了相關調整。首先,將內部工作制定了相關流程。流程化以后,又開展了人員的調整:將育種信息采集技術負責人任命為廠長。通過開展育種數據采集技術培訓,將生產人員同時變為育種技術采集人員,打破了生產人員和技術人員之間的矛盾。同時,為了保證數據收集的準確性,在信息化的基礎上,通過改變生產績效考核方式,將育種和生產融合在一起。在績效考核過程中,將財務人員納入,將配種數據、采購數據、死淘數據、飼草料成本以及人工物料的成本全部加進來,這樣的話,對于育種過程,各個部門均需進行考核,從而達成利益一致。
因此,在信息化基礎上,通過管理方式的改變,把識別、測定、選定、繁育、飼養、管理同步進行,進而實現了生產和育種的充分融合。
劉劍鋒:事實上,無論是家禽育種、生豬育種、肉羊育種,還是其他畜禽育種。育種工作的核心在于性能測定。性能測定是育種上的一個專業術語,反映在今天的話題上來講,性能測定的直接的結果就是育種數據。所以說育種的核心還是數據。數字育種的產生,是育種學科發展到目前階段,跨學科、多技術交叉融合的一個手段體現。我們要從數據的準確性、產生效率及整體挖掘應用等技術上去多方形成合力,來共同助力精準遺傳評估和精準選種選配,這樣才能讓育種成本投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因此,數字化育種技術體系的搭建,是當今乃至未來一段時間,包括育種技術專家、互聯網人工智能技術專家等,共同去探討和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在當前時候,育種需求迎來了最好的發展時機,從國家到每個層面都非常重視。所以我相信這種產學研的結合也好,從多學科的交叉融合也好,一定能助力我們國家實現種業振興的這樣一個宏偉目標。